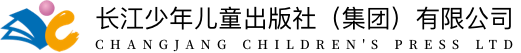抗戰記憶的童年書寫與精神傳承
文/柳偉平
方冠晴的長篇兒童小說《二月謠》以抗日戰爭時期的鄂東地區為背景,依據1938年黃梅少年抗日先鋒隊搗毀日軍機場的真實事件而創作,講述12歲少年板栗為尋找被日軍抓走的父親,與斷臂的戲班班主之女谷雨、家園被毀的少年三壯在淪陷區相遇,三人親歷日軍暴行,最終參與抗日洪流的故事。小說以兒童成長、戰爭記憶與地方文化的深度交融,完成了一次出色的戰爭題材兒童文學書寫。
01.成長、記憶與傳承:兒童視角下的戰爭敘事
劉緒源曾將戰爭題材兒童小說分為兩種模式:一是“孩子的戰爭”,包括《小兵張嘎》(徐光耀)、《閃閃的紅星》(李心田)等,寫兒童在具體戰爭事件中的所作所為;二是“戰爭中的孩子”,包括《少年的榮耀》(李東華)、《滿山打鬼子》(薛濤)、《白棉花》(黃蓓佳)等,寫戰爭環境中兒童的生活狀況。《二月謠》則介于兩者之間,前半部寫“戰爭中的孩子”,后半部寫“孩子的戰爭”,以兒童本位的視角,細膩展現戰爭對童年世界的撕裂與重塑,其核心是三個孩子的心靈成長。板栗本是受奶奶呵護的農家少年,卻因親人遇害,而被迫背負復仇使命。日軍的暴行點燃了他內心的仇恨,而丟失了林姐用生命換來的地圖,則引發他內心巨大的愧疚,從而促使他深入敵境,重繪地圖,完成了從復仇者向主動擔當的抗戰志士的轉變。三壯憨厚遲鈍,戰爭摧毀家園后只求“活著”,而地圖丟失事件帶來的自責,促使他反思自身價值,最終在參與繪制地圖和營救行動中找到了奉獻之路,實現從懵懂到覺醒的成長。谷雨目睹父親被炸死,其復仇意志最為堅定。她與板栗的情誼及照顧二月的行為,都彰顯了其內心的成長與擔當。三位主人公的成長歷程,也是戰爭記憶的文字傳承過程。作者通過他們的視角,為那段被塵封的歷史增添了鮮活的細節,讓今天的兒童能夠觸摸到歷史的溫度,理解和平的珍貴。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這是一部具有歷史價值的記憶文本
02.深層敘事結構與情緒驅動力
作者深諳故事寫作技巧,在小說里埋藏著一個深層敘事結構,即神話、民間故事、童話等敘事作品里萬變不離其宗的基本敘事結構,符合讀者的閱讀期待。小說可分八個部分,按照時間邏輯,首尾相接,環環相扣,組成一個“ 初始世界(田園)→顛覆(日軍入侵)→迷失(個人復仇執念)→覺醒(集體抗爭)→重建(精神家園)”的核心結構閉環。
正如莉薩·克龍所說,“故事無關外部事件,而是關乎內心”,《二月謠》的故事結構并非來自機械地編排,而是靠情緒來驅動敘事,故而能將讀者卷入其中。第一種關鍵情緒是仇恨。第二種關鍵情緒是愧疚。這些情緒的背后,深藏的是孩子們對親人、家國的深愛。仇恨與愧疚的交織,使他們的行動超越冒險,成為肩負使命的抗爭。這種情感轉變讓敘事邏輯更堅實,使讀者深刻理解其行為動機,也極大增強了故事的感染力與說服力。
03.地方風俗與情節的深度交融
《二月謠》中融入了豐富的鄂東風俗元素,并與情節緊密相連,成為重要的敘事基因。小說將大別山脈的飛虎嶺、黃梅西池塘、二套口機場等地理元素融入情節,為作品增添了歷史的厚重感和空間的真實感,其中古塔的多次出現極具象征意義,13 層的八角石塔既是百姓躲避空襲的物理空間,也是一座精神燈塔——當日軍驚嘆“這座千年古塔的結實,怎么也炸不塌”時,作者顯然是通過建筑的不屈來隱喻中華民族的堅韌。此外,榨桐油、捉知了猴、煨砂罐粥、吃蘆葦根等民俗細節,既是兒童戰時生存技能,也是聯結鄉土認同的精神臍帶。
小說中最重要的民俗元素是童謠《二月謠》,這首民謠的三次改編、五次嬗變貫穿整部小說,成為全書的情緒路標。此外,黃梅戲作為當地重要劇種,也參與了小說的敘事。
總之,《二月謠》以兒童視角書寫抗日戰爭,通過情緒推動的敘事和地方風俗的深度融入,成功地塑造了三個在戰火中成長的少年形象,為抗戰記憶保存了最具生命溫度的版本,既讓我們看見中國兒童如何在戰火中唱響永不言敗的“二月謠”,也讓我們反思戰爭的殘酷——小說開頭飛虎嶺中炊煙裊裊、陽光浸染、鳥兒啁啾的安詳場景,在敵后的大古嶺中再次出現,這種日常人間生活的美好恬靜,才是兒童該有的生活環境。

▲ 本文刊發于2025年7月18日《中國出版傳媒商報》第19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