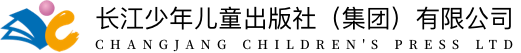自然意象與人性光輝的合奏——評(píng)劉益善長(zhǎng)篇兒童敘事詩(shī)《白鴿花開(kāi)神農(nóng)架》
文/劉祖炎
作為敘事主體的神性山水
《白鴿花開(kāi)神農(nóng)架》的序詩(shī)中寫(xiě)道:“親愛(ài)的少年朋友∕你可知道神農(nóng)架∕那真是個(gè)好地方∕山高林密風(fēng)景如畫(huà)。”作者已然揭示了神農(nóng)架的特殊地位——它不是簡(jiǎn)單的故事背景,而是深度參與詩(shī)歌敘事的主體。
劉益善深諳神農(nóng)架的靈性,他筆下的神農(nóng)架既是具體的地理坐標(biāo),更是承載意蘊(yùn)的神秘符號(hào):“金錢(qián)豹在草叢里打盹∕未抓到獵物正饑餓難熬∕兩人的聲響驚動(dòng)了它∕草叢里突然發(fā)出一聲長(zhǎng)嘯。”寥寥數(shù)筆便讓猛獸躍然紙上,透著鮮活的生命氣息。“綠樹(shù)不搖也不語(yǔ)∕好似傷心悲萬(wàn)分∕對(duì)著白鴿深情望∕像有冤情訴不盡。”則賦予草木細(xì)膩的情感溫度,仿佛它們也能感知悲喜。這種“萬(wàn)物有靈”的書(shū)寫(xiě),更以?xún)和子诶斫獾姆绞剑?ldquo;會(huì)說(shuō)話(huà)的杜鵑”“能指路的松鼠”,讓自然本身的神性與孩童純粹的想象無(wú)縫交融,既貼合孩童的認(rèn)知視角,又暗合著對(duì)自然靈性的敬畏與仰望。
“打豹相識(shí)”一章中,“兩個(gè)少女吃了一驚∕白鴿拉起小梅就跑∕饑餓的豹子哪肯放過(guò)∕對(duì)著小梅縱身一跳”的緊張敘事,將這場(chǎng)相遇嵌入神農(nóng)架的生態(tài)鏈——豹子既是威脅者,也是考驗(yàn)者,它的出現(xiàn)打破了普通格局,讓珙桐的勇毅與白鴿的果敢在生死瞬間綻放。神農(nóng)架的山川草木從來(lái)不是旁觀者,它們以風(fēng)雪、云霧、猛獸、奇花的形態(tài),推動(dòng)著命運(yùn)的齒輪,完成對(duì)人性的試煉。
跨越藩籬綻放的愛(ài)情之花
“珙桐出世”一章里,“給東家送柴擔(dān)水∕給西家澆地播種”似的質(zhì)樸描寫(xiě),勾勒出一個(gè)勤勞善良的人物形象:其父母雙亡的孤苦沒(méi)有令其善意消亡,曾經(jīng)以鋼叉護(hù)佑鄉(xiāng)鄰的勇毅本來(lái)透著悲憫。這種“貧賤不能移”的品格,恰如神農(nóng)架的巖柏,在貧瘠石縫中生長(zhǎng)得愈發(fā)挺拔茂盛。
“白鴿姑娘”一章里,“美如山中的杜鵑∕一雙鳳眼泉水漣漣”的比喻,表現(xiàn)一個(gè)反叛的富家女兒形象:她憎惡父親“對(duì)長(zhǎng)工如狼似虎”的兇狠,悄悄把糕點(diǎn)分給放牛娃;厭煩“深宅大院的金絲雀生活”,總溜出家門(mén)與山民閑談。這份覺(jué)醒并非刻意的叛逆,反倒如“泉水漣漣”般是天性的自然流露——她的善良與對(duì)自由的向往,正是未被世俗塵埃沾染的童心本真。
“碧簪定情”一章中,“若能與她結(jié)成伴侶∕我愿愛(ài)她今世今生”的誓言,表達(dá)跨越階級(jí)藩籬的愛(ài)情:珙桐的碧簪取自神農(nóng)架的綠松石,白鴿的信物是親手繡的山雀帕,前者承載大地的堅(jiān)韌,后者象征生命的靈動(dòng),恰如《詩(shī)經(jīng)》中“投我以木桃,報(bào)之以瓊瑤”的古老饋贈(zèng),在物質(zhì)交換中完成靈魂的守望。
白財(cái)主的阻撓是故事沖突的核心,他的“兇狠貪婪”與珙桐的“正直善良”形成尖銳對(duì)立。這種階級(jí)沖突的書(shū)寫(xiě)避開(kāi)概念化批判,通過(guò)具體場(chǎng)景展現(xiàn):強(qiáng)逼白鴿嫁給“富商的傻兒子”的蠻橫,暗中派人“在山路設(shè)下陷阱”的陰毒,可讓兒童讀者直觀感受壓迫的重量。而珙桐“被暗害化為碧樹(shù)”的悲劇,與白鴿“淚染樹(shù)根化作白花”的結(jié)局,雖帶著宿命的凄美,卻在毀滅中孕育永恒——碧樹(shù)常青,白花不敗,愛(ài)情在自然的懷抱中獲得了超越死亡的生命力。
從自然符號(hào)到精神圖騰
長(zhǎng)詩(shī)中,珙桐樹(shù)與白鴿花作為核心意象貫穿始終,這一樹(shù)一花的神農(nóng)架特有珍稀植物,在詩(shī)中完成了從自然存在到精神圖騰的升華。
珙桐樹(shù)的意象充滿(mǎn)剛健之美。詩(shī)中“樹(shù)干挺直如鋼叉∕枝葉舒展似臂膀”的描寫(xiě),將植物特征與人物品格完美融合——珙桐生前以鋼叉護(hù)佑鄉(xiāng)鄰,死后化樹(shù)仍以枝葉庇護(hù)生靈。這種歷經(jīng)歲月和生死的生命力,正是詩(shī)人發(fā)現(xiàn)的珙桐精神。
白鴿花的意象透著柔韌之美。“花瓣是白鴿的臉∕美如春日的朝霞”的擬人化描寫(xiě),讓植物的形態(tài)美與人物的心靈美統(tǒng)一互見(jiàn)。白鴿生前向往自由如白鴿,死后化作白鴿花仍以潔白昭示人間。這種轉(zhuǎn)化充滿(mǎn)東方美學(xué)的含蓄力量,白鴿的綻放帶著主動(dòng)選擇——“淚染樹(shù)根”是情感的傾注,“滿(mǎn)樹(shù)花開(kāi)”是精神的延續(xù),從而完成了生命的永恒綻放。
除核心意象外,神農(nóng)架的萬(wàn)物都被賦予靈性:打豹情節(jié)中的豹子,既是危險(xiǎn)象征,也是連接兩人的紐帶;“月深沉喲夜風(fēng)起”的環(huán)境描寫(xiě),成為情感的外化——珙桐盼望的焦灼與白鴿思念的凄苦,都在夜風(fēng)與月光中傳遞。這種“物我相融”的寫(xiě)法,讓自然景物成為情感的載體,能使兒童讀者在具體意象中獲得審美感染。
反抗、覺(jué)醒與生態(tài)的三重奏
《白鴿花開(kāi)神農(nóng)架》的深刻之處,在于將多重主題編織成和諧交響,在兒童能理解的敘事中,觸及人類(lèi)文明的永恒命題。
階級(jí)反抗的主題,借由“善惡對(duì)立”的簡(jiǎn)潔敘事傳遞著深刻內(nèi)涵。珙桐幫扶鄉(xiāng)鄰的善舉,與白財(cái)主敲詐勒索的惡行形成鮮明對(duì)照——這種對(duì)比既貼合兒童的認(rèn)知邏輯,又不止于淺層的道德評(píng)判。詩(shī)中珙桐的反抗是符合生活與人物的,并非主動(dòng)掀起革命,而是源于被動(dòng)的守護(hù):當(dāng)豹子威脅村民時(shí)挺身而出,當(dāng)白財(cái)主強(qiáng)搶民女時(shí)奮起抗?fàn)帯_@種“路見(jiàn)不平拔刀相助”的俠義精神,在樸素的行動(dòng)中悄然完成了對(duì)壓迫的反抗。而最終“碧樹(shù)護(hù)佑山村”的結(jié)局,更傳遞出“善良終將戰(zhàn)勝?gòu)?qiáng)權(quán)”的信念,為兒童讀者悄然播下希望與理想。
性別覺(jué)醒的主題在白鴿身上得到詩(shī)意呈現(xiàn)。她不是等待拯救的公主,而是主動(dòng)追求自由的獨(dú)立個(gè)體:溜出深宅與山民交往是對(duì)身份的突破,拒絕富商聯(lián)姻是對(duì)命運(yùn)的抗?fàn)帲?ldquo;與小梅緊相依訴說(shuō)不平”是女性互助的覺(jué)醒。這種形象塑造打破了傳統(tǒng)兒童文學(xué)中“富家女必驕縱”“女性必柔弱”的刻板印象;白鴿的選擇證明環(huán)境無(wú)法完全禁錮天性的自由,這是女性命運(yùn)抗?fàn)幍纳鷦?dòng)注腳。
生態(tài)寓言的主題具有鮮明的時(shí)代價(jià)值。詩(shī)中“珙桐從不濫殺生靈”“白鴿與鳥(niǎo)獸對(duì)話(huà)”的描寫(xiě),傳遞出“萬(wàn)物平等”的生態(tài)理念;而兩人最終化身為樹(shù)與花的結(jié)局,更是“人與自然共生”的極致表達(dá)。這種意識(shí)不是生硬的說(shuō)教,而是如“泉水滲透土壤”般自然融入情境:當(dāng)兒童讀到“白花碧樹(shù)緊相連”時(shí),會(huì)直觀感受到人類(lèi)與自然的血脈相連,讓生態(tài)保護(hù)的理念在美的熏陶中深入人心。
質(zhì)樸語(yǔ)言中的詩(shī)性張力
作為一部?jī)和瘮⑹麻L(zhǎng)詩(shī),《白鴿花開(kāi)神農(nóng)架》的語(yǔ)言藝術(shù)達(dá)到了“深入淺出”的境界。“月深沉喲夜風(fēng)起∕夜風(fēng)颯颯語(yǔ)凄凄”的疊詞運(yùn)用,如民間歌謠般朗朗上口,既符合兒童的語(yǔ)言接受習(xí)慣,又營(yíng)造出“言有盡而意無(wú)窮”的意境。這種韻律感讓詩(shī)歌更適合朗誦,兒童在朗讀中能自然感受情感的起伏。而“打豹相識(shí)”的急促短句傳遞緊張,“情深誼長(zhǎng)”的舒緩長(zhǎng)句流露溫情,語(yǔ)言節(jié)奏與情節(jié)發(fā)展形成了同頻共振。
作品的結(jié)構(gòu)采用傳統(tǒng)敘事詩(shī)的線性脈絡(luò),從“珙桐出世”到“白鴿花開(kāi)”,十章內(nèi)容層層遞進(jìn),如神農(nóng)架的山路般蜿蜒向前,既保持了故事的完整性,又留下足夠的想象空間。序詩(shī)與尾聲的首尾呼應(yīng),形成“起承轉(zhuǎn)合”的閉環(huán)結(jié)構(gòu),讓整個(gè)故事在“傳說(shuō)——現(xiàn)實(shí)——傳說(shuō)”的循環(huán)中獲得超越時(shí)空的意義,這種結(jié)構(gòu)安排使兒童能清晰把握故事脈絡(luò),同時(shí)感受敘事的完整性。
《白鴿花開(kāi)神農(nóng)架》的尾聲中說(shuō):“來(lái)吧,少年朋友∕舉起夏令營(yíng)的旗幟∕背起你的小書(shū)包∕唱一支走向自然的歌曲∕親愛(ài)的少年朋友∕神農(nóng)架已揚(yáng)起手臂∕那一樹(shù)一樹(shù)的白鴿花∕在呼喚你在歡迎你。” 這部作品既能讓孩子讀懂純真,也能讓成人讀出歲月的滄桑。相信《白鴿花開(kāi)神農(nóng)架》這朵文學(xué)之花,會(huì)綻放在孩子們的心田。
(本文作者劉祖炎,湖北作家,曾從事編輯記者工作,著有《神農(nóng)架之戀》《神農(nóng)架筆記》《到神農(nóng)架去》《神農(nóng)架印象》《黑暗傳》《胡崇峻傳》等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