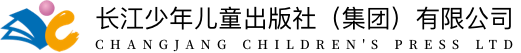李少白的兒童詩表現出出色的基于兒歌和民間童謠的韻律感、節奏感和清新之氣,也展示其童心之天真以及一位兒童詩人對兒童的誠摯之愛;另一方面,李少白近年的創作呈現出一種活潑的現代藝術之新質,極大地拓展了童詩的表現疆域,在藝術技法上與金子美鈴的童謠及謝爾·希爾弗斯坦、斯蒂文森的兒童詩等展開對話。這種藝術新質在其兒童詩集《世界對我說》(長江少年兒童出版社,2024版)中得到了集中展現。
回歸童心即回歸驚奇:用孩子的語言,叩問世界的奧秘
詩集副書名為《理趣童詩99首》,如何理解兒童詩之“理趣”?必是“理趣”蘊含于“童趣”之中。李少白的童謠及兒童詩的藝術追求,其一在音樂性、知識性、品格養成、文化熏陶、童心呵護等多維價值訴求的融合,其二在想象力、詩意和哲理的融合。《世界對我說》的藝術新變表現在,“溫柔敦厚的師長形象”隱藏得更深,他解放了童心,解放了語詞,解放了韻律,讓童心、語詞與韻律自由出場。于是,他發現了童年精神作為審美對象的藝術特質:簡單明了而又意味深長。
童詩的哲學意味源自兒童視角所展示的直面事物本質的力量。“當了這么多年的啟蒙老師,寫了這么多年的兒童詩,我終于信服了這兩句話——‘孩子是天生的詩人’‘孩子是天生的哲學家’”,李少白在后記中如是說。回歸童心即回歸驚奇,即回歸詩歌,并觸及哲學。這位一輩子為孩子寫詩、寫歌的詩人沉浸在基于童年哲學之上的語詞與思緒自由流淌的喜悅之中,“跑向天邊的那條線/發現一片/開滿小花的草原//跑向天邊的那條線/找到一汪/落滿星星的清泉//跑向天邊的那條線/遇見一座/童話般的古老宮殿//跑向天邊的那條線/來到一個/百果飄香的莊園//小馬不停地/奔跑/奔跑/向前/向前//跑向天邊的那條線”(《跑向天邊那條線》)。
兒童主體性的喚醒:在微小事物中發現自我
詩人復歸于孩童——孩童視角使詩人重新“發現”宇宙萬物本然自足的秩序之中所生發的無窮意味,如《樣子》,“我喜歡看企鵝走路的樣子/像一個不倒翁在滑冰//我喜歡看小雞啄食的樣子/尖嘴兒嘟嘟嘟在地上彈琴//我喜歡看青蛙坐在荷葉上的樣子/小不點兒也有些老虎的威風//看著它們可愛的樣子/我真想看看自己/走路的樣子/吃飯的樣子/讀書的樣子//看看自己的樣子”;又如《都很可愛》,“一朵花兒謝了/一粒青果冒出來//一兜小草枯黃了/一支嫩芽綠出來//一個蛋殼破了/一只小鳥跳出來//一只青蛙老了/一群蝌蚪游過來//昨天的太陽落下了/今天的太陽升起來”,以小兒之目靜觀萬物,而以詩人之筆寫之,萬物有序,萬物驚奇,萬物可愛,平常語中飽含詩人對人世間的深情摯愛,亦提請兒童“看見”與己相關聯的一切。
“看見”是愛的開始。“墻上一兜小草/墻角一兜小草//沒人去看/沒人去瞧//自有陽光照它/也有露水喂它//墻上的小草開花了/墻角的小草開花了//蜜蜂知道/蝴蝶知道//每一兜小草/都會開花”(《小草開花》),“苔花如米小,也學牡丹開”(袁枚《苔》),這是對微小事物的發現與接納,也即對自我的發現與接納。詩人再次對他的小讀者說,“自己愛自己/從小就學會”(《蜻蜓點水》)。
詩人對于兒童主體性的喚醒親切、自然,如《一步一步自己走》,“太陽沒有腳/一個輪子滾著走//月亮沒有腳/變成小船劃著走//云兒沒有腳/風兒幫忙推著走//我有一雙腳/一步一步自己走”。孩童在念唱之際,所了悟的甚多,這正是給孩子最初的書應有的樣子。
萬物與“我”相關聯:在孩子心中種下關愛的種子
世界之深邃浩瀚、搖曳多姿,不僅體現為個體精神之獨立自主,還體現在“關系”之中。故《一個人的時候》并非真的一個人,“一個人坐在房子里/布熊躺在床頭陪我/掛鐘移著指針陪我/風兒掀動窗簾陪我//一個人在晨光里讀書/小鳥在綠葉間讀我/睡蓮睜開眼睛讀我/蟈蟈兒停住歌聲讀我//一個人在月光下散步/星星在云縫里看我/螢火蟲圍過來看我/小耗子趴在洞口看我”。“我”不是孤零零的“我”,與萬物相互聯結,便“看見”了一個生機盎然、處處與“我”相關聯的世界。“我”之為“我”,的確與身邊一切事及一切人有關,也與看不見的遠方有關。
打爛了碗片,卻沒有把它包起來,那么,“那些碎瓷片兒呢/不會傷著別人的手吧/不會劃破小貓小狗的腳吧”(《一會兒的事》),從童年的同情心和理解力出發,詩人筆下生長出一種嶄新的童年生態觀。萬物與我同一,是原初思維的特征,其中卻蘊含深刻的哲學命題,詩人用很多詩篇傳達了這一理念。“我和燕子/在同一個屋檐下/我和魚兒/共用一個游泳池//我和小鳥/共一片藍天/我和種子/同一方土地//我和藏羚羊/同飲一江水/我和蜜蜂/共嘗花中蜜//我和螢火蟲/同享夜晚/我和太陽/共度朝夕//我和大家/共一個地球/地球和我/都是宇宙的孩子”,《美美與共》,和而不同,“我”與宇宙萬物雖各有不同,卻在同一個宇宙之中,是生命共同體。詩人以接通兒童心理與兒童思維的詩歌,引領兒童讀者獲悉并踐行“美美與共”的生態理念。
以小見大:領悟生活的真諦和愛的真諦
詩人也從兒童視角出發,傳達“以小見大”的辯證法。小兒之小,實為大,這是兒童哲學的核心要義。
“小草說:我很小/大地說:你不小/是你把荒原綠遍了//水滴說:我很小/大海說:你不小/是你把江河湖海盛滿了//種子說:我很小/土壤說:你不小/是你把生命延續了”(《小的美好》),“別以為娃娃魚很小/它是恐龍時代的遺老”(《小的不可小看》),“有些東西/看上去很小/其實,它/很大很大/就像那天上的星星//有些東西/看上去很大/其實,它很小很小/就像那吹大了的肥皂泡”(《大和小》),詩人頌揚“小”之奇妙,“小”之力量。
小兒不小,“你的眼睛里/有一片日月//你的心中/有一個小宇宙”(《世界對我說》)。《倒霉的一天》《生病的時候》《有點兒煩的事》《羨慕》《有,還得有》《沒有我 有了我》《母女倆》《看山》等詩篇,均從兒童的生活體驗出發,從生活的辯證法中領悟生命的真諦和愛的真諦。
以豐富的藝術表現詮釋“孩童宇宙之深邃”
詩人以前所未有的題材拓展和藝術表現,詮釋“孩童宇宙之深邃”。
《巨人站在哪兒》彰顯稚童之想象力,“房子是人蓋出來的/輪船是工廠里造出來的/果子是樹上結出來的/蜂蜜是蜜蜂釀出來的//天上的星辰/腳下的土地/海洋里的水/是誰弄出來的呢//如果是巨人/打造出一切/這位巨人的腳/站在什么地方呢”。
《天那邊》是對好奇心的頌揚,“天那邊有什么呢/我問爸爸/爸爸問天文望遠鏡/望遠鏡眼睛很長/看得見月亮上的環形山//天那邊有什么呢/我問環形山/環形山問太陽/太陽的火眼金睛/看得見銀河//天那邊有什么呢/我問銀河/銀河問星云/星云急急忙忙趕路/邊走邊說/天那邊有什么/我這不急著/去尋找嗎”。
而《同桌》則描寫少年心思之微妙有趣,“排座位了/我想同桌的/最好是個女生//為什么呢/是她不會欺負人/是她愛把桌椅抹干凈/是她常帶著小點心……//不!不/還有,還有/還有什么呢/其實,我也說不清”。
《錯別字》舉重若輕,以兒童視角反觀現代文明之荒謬:“炮蛋/炸蛋/原子蛋//孩子/你的“蛋”字/寫成錯別字啦//我是這樣想的/要是改用這個“蛋”字/多好呀//我錯了嗎”。
再看《螞蟻打個哈欠》,“螞蟻打個哈欠/吹起鵝毛一片//鵝毛飄飄落地/壓住老鼠胡須//老鼠鼻子癢癢/打了一個噴嚏//噴嚏響得像放炮/嚇得花貓把命逃//快快逃,慌了張/一頭撞上黃鼠狼//黃鼠狼,放個屁/旋渦風,平地起//要問這風哪里來/只怪螞蟻小哈欠”。詩人如孩童般機巧、頑皮,語言狂歡中流露孩童般自由的想象力和游戲精神,可謂“無意思之意思”的佳作。
這些詩有的可稱哲理詩,有的可稱寓言詩,有的可稱童話詩,有的可稱荒誕詩,以小見大,弦外有音,讀來或童趣盎然,或含蓄蘊藉,或充滿思辨,或荒誕幽默,充分展現了李少白兒童詩歌藝術的豐富性,是當代兒童詩的重要收獲。
(本文作者系湖南師范大學文學院教授,南丹麥大學安徒生中心訪問學者,湖南省兒童文學學會副會長,湖南省童話寓言研究會副會長,中國兒童文學研究會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