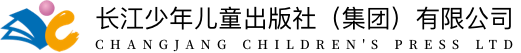帕米爾高原的鷹笛穿過(guò)云層,穿透稀薄的氣流,與拼力飛向帕米爾雪山的雄鷹振翅合為一體,與塔吉克族孩子天籟般的童聲交織在一起——這是作家畢然在《雛鷹合唱團(tuán)》中為讀者創(chuàng)造的一個(gè)富有象征意味的視聽(tīng)意象。這部小說(shuō)以漢族支教老師為塔吉克族少年兒童組建雛鷹合唱團(tuán)的故事為載體,構(gòu)建了一曲多聲部的成長(zhǎng)敘事交響。漢族支教老師與塔吉克少年的相遇,不僅是兩種文化的交流對(duì)話,更是現(xiàn)代教育理念與邊疆民族傳統(tǒng)的創(chuàng)造性融合。作家畢然以其豐厚的創(chuàng)作經(jīng)驗(yàn),特別是有《樓蘭密碼》《生死樓蘭》等邊疆非虛構(gòu)歷史文化散文題材的深厚積淀,在兒童文學(xué)這一創(chuàng)作形式中,注入了文化人類學(xué)的視野與詩(shī)性的哲學(xué)思考。

《雛鷹合唱團(tuán)》的敘事結(jié)構(gòu)頗具特色。少年香港、馬克、艾山和啞巴女孩妮莎及支教老師伍子健、秦歌,六位不同的敘述者站在各自的角度,看待成立合唱團(tuán)、與夢(mèng)想一起飛翔的核心話題,作品呈現(xiàn)出精妙的“蓮花瓣式”美學(xué)特征。小說(shuō)以合唱團(tuán)的組建與發(fā)展為中軸,每一章節(jié)如同蓮花瓣般向外舒展,各自獨(dú)立又緊密相連,展現(xiàn)不同人物的生命體驗(yàn)和情感抒寫。這種結(jié)構(gòu)既保持了兒童文學(xué)應(yīng)有的線性敘事的清晰度,又通過(guò)多視角敘事豐富了文本的層次感。作品以塔吉克族少年兒童的視角展現(xiàn)了他們對(duì)鷹笛、手鼓、鷹舞等民族文化的熱愛(ài),及對(duì)外部世界的憧憬和向往;妮莎的視角又為讀者打開(kāi)了塔吉克族殘疾女孩特有的內(nèi)心世界。漢族支教老師秦歌和伍子健的視角則傳遞了教育者的理想、情懷與困惑。畢然巧妙地將這些視角編織在一起,如同塔吉克刺繡般繁復(fù)而和諧,使小說(shuō)在保持兒童文學(xué)可讀性的同時(shí),具備了復(fù)調(diào)小說(shuō)的藝術(shù)深度。

音樂(lè)在小說(shuō)中既是敘事的推動(dòng)力,也是重要的隱喻系統(tǒng)。合唱團(tuán)的排練曲目從塔吉克族民歌《花兒為什么這樣紅》到伍子健和秦歌創(chuàng)作的從心而發(fā)的歌曲演進(jìn),象征著個(gè)體成長(zhǎng)與民族認(rèn)同的雙重變奏。畢然對(duì)音樂(lè)描寫的處理極具匠心,她將抽象的旋律轉(zhuǎn)化為可感的視覺(jué)形象:“那聲音輕盈又悠遠(yuǎn)、干凈而通透,好似慕士塔格山上繚繞的白云。”這種視聽(tīng)結(jié)合的通感修辭不僅符合少年兒童的感知方式,更暗示了藝術(shù)教育如何照亮邊疆少年的精神世界。值得注意的是,小說(shuō)中的音樂(lè)不是單向的傳授,而是雙向的文化交融——漢族教師帶來(lái)音樂(lè)理論和技巧,塔吉克族孩子則貢獻(xiàn)了獨(dú)特的民族音樂(lè)記憶,這種互動(dòng)打破了文化傳播中的中心主義迷思。
《雛鷹合唱團(tuán)》的文學(xué)語(yǔ)言呈現(xiàn)出獨(dú)特的韻律美,既保持了兒童文學(xué)的明快節(jié)奏,又融入了塔吉克族語(yǔ)言的音樂(lè)性。畢然在對(duì)話中適當(dāng)使用經(jīng)過(guò)藝術(shù)加工的少數(shù)民族語(yǔ)言表達(dá),如“海熱提卡”(加油)等,既增強(qiáng)了地域真實(shí)感,又不會(huì)造成閱讀障礙。在敘述語(yǔ)言上,她善于使用短句和重復(fù)修辭模擬童聲合唱的節(jié)奏,這種語(yǔ)言風(fēng)格既適合兒童閱讀,又具有詩(shī)性的美學(xué)價(jià)值,體現(xiàn)了作者對(duì)文學(xué)形式的高度自覺(jué)的審美意識(shí)。書中一再出現(xiàn)的飛翔的鷹、鷹舞和雛鷹合唱團(tuán)的名字,這些意象巧妙地將塔吉克文化圖騰與音樂(lè)體驗(yàn)融為一體。“鷹笛聲聲,從我的胸腔沖向藍(lán)得虛幻的天空,沖向慕士塔格山。我看見(jiàn),無(wú)數(shù)只鷹在高空中盤桓。”
作為一部現(xiàn)實(shí)主義作品,《雛鷹合唱團(tuán)》對(duì)邊疆教育現(xiàn)狀的呈現(xiàn)既有溫暖的亮色,也不回避現(xiàn)實(shí)的陰影。馬克因家庭重負(fù)想放棄上學(xué),又在放羊的路上背著課本讀書,想去北京求學(xué),又怕路費(fèi)給家庭帶來(lái)困擾,具有矛盾的心理;艾山由于父親去世、母親生病,產(chǎn)生了巨大的心理壓力,一度想輟學(xué)打工照顧家人;香港的父親不贊同孩子學(xué)藝術(shù),認(rèn)為“唱歌跳舞忙了半天”,還是“賺不來(lái)為奶奶做手術(shù)的錢”……這些生活困境細(xì)節(jié)呈現(xiàn)了塔什庫(kù)爾干物質(zhì)條件的局限和困頓。支教老師秦歌因高原反應(yīng)導(dǎo)致的身體疾患,無(wú)論是流鼻血還是后來(lái)的癌癥,折射出現(xiàn)實(shí)生活中幾乎每個(gè)人都背負(fù)著命運(yùn)的鐐銬——一面苦苦求索,另一面又自發(fā)地對(duì)著太陽(yáng)起舞、歌唱。小說(shuō)通過(guò)家長(zhǎng)對(duì)教育的疑慮和渴求,反映了傳統(tǒng)文化與現(xiàn)代價(jià)值觀的張力。但畢然并沒(méi)有將小說(shuō)陷入悲情敘事,而是以建設(shè)性的態(tài)度展現(xiàn)問(wèn)題解決的過(guò)程:地方政府對(duì)合唱團(tuán)的支持,體現(xiàn)了國(guó)家對(duì)邊疆教育的重視;民營(yíng)企業(yè)家給予陷入困境孩子雪中送炭的援助,無(wú)論是一雙靴子還是一張機(jī)票,都體現(xiàn)了人類命運(yùn)共同體的悲憫情懷。在皮勒深山的求學(xué)者跋山涉水、翻山越嶺的執(zhí)著堅(jiān)持,則彰顯了生命自身向陽(yáng)而飛的韌性。這種平衡的敘事姿態(tài),使作品既具有現(xiàn)實(shí)主義的力量,又保持了兒童文學(xué)應(yīng)有的希望之光。
在文化認(rèn)同的構(gòu)建上,《雛鷹合唱團(tuán)》做出了富有創(chuàng)新性的探索。小說(shuō)中的塔吉克族少年不是被動(dòng)接受主流文化的“他者”,而是積極的文化詮釋者和創(chuàng)造者。畢然通過(guò)這種藝術(shù)融合表明,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shí)不是消除差異的整齊劃一,而是“各美其美,美美與共”的共生狀態(tài)。當(dāng)孩子們?cè)谖枧_(tái)上用塔吉克語(yǔ)和漢語(yǔ)演唱時(shí),他們實(shí)際上在實(shí)踐一種更具包容性的身份認(rèn)同——這或許正是小說(shuō)最重要的當(dāng)代意義。
從《雛鷹飛向帕米爾》到《雛鷹合唱團(tuán)》,畢然的創(chuàng)作呈現(xiàn)出清晰的美學(xué)發(fā)展軌跡。她早期的邊疆題材作品更注重異域風(fēng)情的展示,而在這部新作中,則更加關(guān)注普遍人性與特殊文化背景的交融。這種轉(zhuǎn)變使《雛鷹合唱團(tuán)》超越了地域文學(xué)的局限,觸及了更為本質(zhì)的成長(zhǎng)命題:如何在保持文化根性的同時(shí)擁抱更廣闊的世界?如何將傳統(tǒng)的饋贈(zèng)轉(zhuǎn)化為創(chuàng)新的資源?這些問(wèn)題不僅關(guān)乎塔吉克族少年兒童,也是全球化時(shí)代所有少年兒童必須面對(duì)的課題。
《雛鷹合唱團(tuán)》的結(jié)尾,孩子們站在更大的舞臺(tái)上,他們的歌聲“對(duì)著帕米爾冰山之父——慕士塔格山,對(duì)著石頭城上空飄蕩的陣陣天風(fēng)”。這一場(chǎng)景構(gòu)成了一個(gè)富有象征意義的成長(zhǎng)儀式,標(biāo)志著邊疆少年從文化邊緣走向中心舞臺(tái)的自我實(shí)現(xiàn),這中心舞臺(tái)則是所有合唱團(tuán)演出奔赴的高地——帕米爾高原。畢然以她特有的文學(xué)敏感和人文關(guān)懷,為我們記錄了這一精神旅程中的淚水與歡笑。在這個(gè)意義上,《雛鷹合唱團(tuán)》不僅是一部?jī)?yōu)秀的兒童文學(xué)作品,更是一曲關(guān)于文化對(duì)話與生命成長(zhǎng)的動(dòng)人詩(shī)篇。

▲本文發(fā)表于2025年5月16日《中國(guó)新聞出版廣電報(bào)》綜合書評(píng)第7版,發(fā)表時(shí)有刪改。